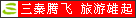读了何志刚先生的《访古览胜戴兴寺》后,我被文中蔡君所称“戴兴寺有三古值得宣扬,一是泥塑古造像弥勒佛,二是十多方明清碑石木匾,三是两株珍稀古树”深深吸引,故在闲暇之时,专门去戴兴寺寻访。
泥塑弥勒幸得存
泥塑古造像弥勒佛,在戴兴寺北小院东殿供奉。
弥勒佛,也称弥勒尊佛、未来佛。我们如今看到的“弥勒佛”,实际是按照布袋和尚的形象塑造的。
据资料记载,布袋和尚是五代时期明州(今宁波)人,世传为弥勒菩萨化身,身体胖,眉皱而腹大,出语无定,随处寝卧。他常以杖挑一布袋入市,见物就乞,别人供养的东西统统放进布袋,却从来没有人见他把东西倒出来,那布袋又是空的。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哲宗皇帝赐布袋和尚为“定应大师”之后,天下寺院逐渐开始供奉。
戴兴寺供奉的弥勒佛,虽不算高大宽壮,但长长耳垂、圆圆大肚、袒胸露腹、笑容可掬的迎接着八方来客,让人喜欢十分。再加上门口楹联上: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显示着弥勒佛宽大的胸怀,因此而受到各方人士的欢迎。
据说这尊近500年的弥勒佛泥塑造像,在“文革”中是被信众用砖砌护在洞内,在外面大大的写了一个“忠”字才逃过劫难的。不然,我们就可能无法看到其尊容了。
此神此情,确实可称戴兴寺之第一古。
碑石牌匾诉沧桑
匾额是古建筑的必然组成部分,相当于古建筑的眼睛,是悬挂于门屏上作装饰之用,反映建筑物名称和性质,表达人们义理、情感之类的文学艺术形式,也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精品。几千年来,匾额把中国古老文化流传中的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以其凝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深远的寓意,成为中华文化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戴兴寺檐下的匾有明崇祯九年(1636年)的“急周同道”、康熙二十年(1682年)的“仁让超厚”、康熙年间的“德风远布”“善世法门”、道光五年(1825年)的“永锡祚胤”、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僧会司”、光绪十八年的“情周惠至”、光绪年间的“尘缘悟净”等等。碑石两块分别是宣统二年(1910年)的修寺碑记和戴兴寺住持的题词碑。这些匾额碑石,年久的已有370多年,年短的也已百年有余,个个书法精湛,言简意赅,反映了当年的时代背景与民俗民风,不仅是历代书法艺术的展示,更是历史与古老文化的记录,是中国文辞之美与工艺之美的集中体现。
戴兴寺的匾额,作为榆林古城建筑的一部分,因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已经成为今天研究古城文化的实物例证。
此物此文,确实可称戴兴寺的第二古。
降龙古木谱传奇
两株珍稀木瓜树,生长在南小院西墙边。
木瓜树又名木梨、降龙木等,属于落叶乔木,在树木分类学上属无患子科,中文名为冠果,是一种优良的木本油料树种,开花多,结果少,有“千花一果”之说,因此比较珍贵。由于木瓜树姿态各异,大多为灌木状,极少长成乔木,整株又可入药,经济价值很高,所以很受群众喜欢。但主要生长在中国的中部地区,北方较少。
戴兴寺的木瓜树,由地表分为两株,高约9米,树龄约500年,人们称之为夫妻树。妻树居北,粗可盈抱,两米多高之上枝分两方,舒展向上;夫树居南,稍细,挺拔的腰杆有三米多,直冲而上。从南北方向看,二者相依生长,似如一株;从东西方向看,夫树直立,妻树略靠,枝桠之上,成为一体。夫妻间相依为命,不同方向观察,有不同的分合之形状,人们便皆谓之神奇。
此木此景,确实可称戴兴寺的第三古。
戴兴寺虽然大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原貌,但上述三古各有特色,数百年来与建筑同在,为寺院增辉,值得我们保护与宣扬。


![百变“鸡蛋饼”[图]](http://www.sanqinyou.com/uploadfiles/2014-06-19/20140619_205843_653.jpg)
![陕北黄酒[图]](http://www.sanqinyou.com/uploadfiles/2014-06-19/20140619_205636_93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