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陕西旅游年票一卡通》包含98城市408家景区的强大阵容,一卡游遍全国。定价98元/张。
【点这里订购(支持邮寄)】【点这里淘宝购买】
您现在的位置:三秦游网>>民俗风情>>正文
吼秦腔(2)
2012-4-10 8:52:33 来源:西安日报 点击:
次 进入论坛
看戏是农业文明时代人们文化消费的首要选项,戏台也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文化启蒙的重要平台,被称为“高台教化”。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窦府巷口的戏台》,其中这样记叙自己儿时看戏的经历:“对我、以及和我一样的小孩子,最初关注的无疑并不是戏剧艺术甚或戏剧故事本身,而是戏台上下的新奇和热闹”,“但慢慢的,随着年龄的渐大,舞台上那些人物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开始吸引我、感动我,并逐渐成为我熟悉的人物和故事,也因此,我最初的是非观念的形成,我最早的对善恶忠奸的认定,想必会有着在窦府巷口那座简陋土台上演出过的戏文打下的深深烙印!”
戏曲更为紧要的功能,还在于许多年来,它一直是人们或自娱自乐、或宣泄感情的有效手段。所谓“诗言志,歌咏言,言之不足则长言之,长言之不足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对一个西安人(尤其是农业文明时代的西安人)而言,当他或有一肚子的欢乐需要张扬,或有一肚子的悲愤亟待倾诉,或有一肚子的委屈想去宣泄……不说是首要选项,起码也是选项之一吧,便是扯开嗓子,把一段自小听到大、听到老,已经烂熟于心的秦腔戏文唱将起来;当然,戏文的内容肯定得符合演唱者的心境——此之谓吼秦腔是也。西安土话中称此为“借他人的灵堂,哭自己的恓惶”;相反的情况,则可称之为“借他人的喜事,秀自己的欢畅”。
至于为何称吼秦腔而不说唱秦腔?我想原因无非有二:一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唱一方戏,在黄土文化氛围中诞生的秦腔,其声腔——尤其是须生、黑头、花脸的声腔,高亢激越,苍凉雄浑,好像唯有一个“吼”字,才能把演唱者的行状表现得惟妙惟肖;二是吼秦腔者,又大都是指剧场以外的非专业演唱,此等人众,不曾接受精到的专业训练,发声行腔多呈原生态,而对原生态演唱的描摹,当然也是“吼”字更为合适。
坊间有俚语曰:“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这都是旧时风光了。如今,八百里秦川早已是树绿花红,一片锦绣,而随着社会的进步,老百姓的文化消费市场也越来越丰富多彩,秦腔的地位远不如当年显赫。不过,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秦腔必将千秋万代地流传下去。在环城公园的树荫下、花丛旁,不就常常有吼秦腔者引吭高歌吗?熟悉的唱段,沧桑的声腔,似乎混响着久远历史的回声和西安前行的步点,让人慨叹,令人振奋……
附言:岳钰教授是我敬重的画家,有一段时间,我常去他的画室喝茶、聊天,说起古城旧事,两个西安老汉往往感慨多多。也曾有过合作一把,用图文相配的方式来强化西安城市记忆的想法,但由于我的懒散,一直未能实施。这一次,有西安日报的督促和帮助,我和岳钰教授的夙愿得以实现,真是不亦快哉!□商子雍(陕西)
编辑:秦人
发表/查看评论 共
条
相关链接
三秦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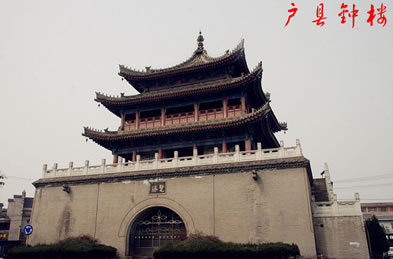




![盛开的油菜花让汉中风景更靓丽[图]](http://www.sanqinyou.com/uploadfiles/2012-04-10/20120410_093212_690.jpg)
![瓜子皮粘出《清明上河图》[图]](http://www.sanqinyou.com/uploadfiles/2012-04-10/20120410_084259_508.jpg)
![西安四月多处樱花正怒放 赏花何必扎堆[图]](http://www.sanqinyou.com/uploadfiles/2012-04-09/20120409_183713_162.jpg)
![西安旅游纪念:手绘“忒色西安”钟楼南门大雁塔一眼就能找到[图]](http://www.sanqinyou.com/uploadfiles/2012-04-05/20120405_102315_152.jpg)
![陕西自驾游新线路:寻根之旅[图]](http://www.sanqinyou.com/uploadfiles/2012-02-02/20120202_232743_926.jpg)
![陕西自驾游新线路:丝绸之路之旅[图]](http://www.sanqinyou.com/uploadfiles/2012-02-02/20120202_232619_170.jpg)



